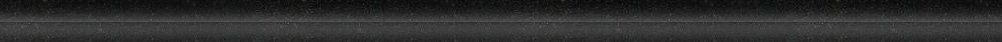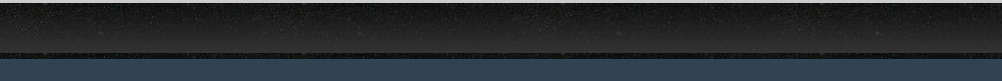圣诺医药不算是线年最后一天在港交所挂牌,算起来已经是第48家18A公司了,赶上了biotech上市潮的尾声,当时募集资金大约5.5亿港元。
圣诺医药独步江湖的技术是siRNA药物开发。要是早两年上市,光是拿出几个投资者都看不懂的科技名词,这家公司的总市值也不止50亿港币。不过还好,虽然募资不多,圣诺医药花钱倒也不算大手大脚,这两年都是亏了1亿美元不到。
而且,圣诺医药董事会还是很有前瞻性的,早就设计好了到2025年底的资金规划。去年年底,董事会一看账上钱不多了,马上决定减少经营活动,同时宣布:计划赎回部分认购基金。
圣诺医药所谓的“认购基金”是2022年底买的,当时公司账上有1亿多美元,董事会拍板决定买私募基金,一共分两次买了2000万美元认购了一个独立投资组合。
这件事本身没什么毛病。圣诺医药所买的私募基金业内有点小名气,中文名叫“好赞基金”。这个私募曾在2022年底连续两次出手,成为港股上市公司思路迪医药和星空华文的基石投资人,总的投资额大约1500万美元。
好赞基金这两笔投资的出手时间和圣诺医药的缴款时间十分接近,大概率,这个基金是拿了圣诺的钱去投了两家新IPO的企业。
可惜2023年的港股市场早就不是两年前可比,而且越走越差:思路迪医疗发行价接近25港元,目前剩下4.48港元;星空华文发行价26.5港元,目前股价4.14港元。两家公司都只剩下两折不到。
港股的基石投资者,就好像A股IPO前的机构投资者那样是有锁定期的,一般是3个月到1年。好赞基金投星空华文就承诺锁定一年。出现上市破发一路下行的走势,只能看着它跌。
但是,这种行情下,圣诺医药在2023年底还对好赞基金的这笔投资进行了测算,认为投资的2000万美元妥妥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因此没有做任何减值。也不想想自家股价都腰斩了
直到今年上半年过完,圣诺医药似乎才突然慌起来,因为好赞私募基金突然宣布:可能会违约。
要不是圣诺医药公告过:基金投资经理顾玮、管理人毕霞和孙银花均为独立第三方,还真以为这中间有点啥猫腻。
说句题外话,圣诺医药这家公司运气线月,美国硅谷银行事件中,国内有几家biotech企业有钱存在这家银行里,其中就包括了圣诺医药,涉及金额330万美元。
目前,圣诺医药还没确认好赞基金的投资损失,但去年年报上公司账面现金和现金等价物只有2388万美元。如果这笔2000万美元的基金投资收不回来,公司可能会陷入资不抵债的境地。
Biotech企业里,像圣诺医药这样的并不少。这些公司在来财如长天顺测速网址江流水之时,仿佛老鼠掉进米缸里,钱多得不知道怎么花才好,完全偏离IPO之时的募资规划。
圣诺医药的募资用途规划倒是挺详细的,给核心产品STP705的研发和生产留足了大约21%,其他进度还早的管线%,其他用于生产基地建设和留作销售费用。
2000万美金的投资收不回来,看似是个笑话,但又何尝不是投资者抛弃biotech的一个理由:“你们管这叫医药创新?”
7月9日,康诺亚宣布将2款自主开发的双特异性抗体CM512、CM536的大中华区外全球权益授权给Belenos Biosciences。
康诺亚将获得1500万美元的首付款和近期付款、最高1.7亿美元的里程碑款以及销售净额的分层特许权使用费,同时,全资附属公司一桥香港将获得Belenos约30.01%的股权。Belenos Biosciences另外由隶属于OrbiMed的基金持有50.26%,康诺亚董事长兼执行董事Bo CHEN则是董事会四名成员之一。
已经有企业走通了这条路——2024年上半年,有两家核心资产来自中国的biotech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
其一是1月上市的ArriVent,其核心资产是从艾力斯引进的第三代EGFR-TKI(伏美替尼),其二是两周前上市的Alumis,核心资产是来自海思科子公司FT集团的一款高选择性且具备Best-in-Class潜力的TYK2抑制剂。
“ArriVent(上市)说明,一个单纯的中国创新药资产,也能在美国受到投资人以及二级市场的认可,这给了大家很多信心。1月开始,很多美国大基金都来跟我们联系,也想做这种模式。”近日的首届美国华人生物医药科技协会上,BFC Group董事陆琦雯说到,“当然,投资人‘买账’也是看到很多MNC在中国购买创新药资产,也赞同现在中国创新药资产质量很高。”
BFC Group专注于医疗行业,超70%聚焦于创新药领域,主要有融资、并购、BD、咨询四大业务,版图涉及中国、美国和欧洲,近年来撮合了超100起医药交易,累计交易金额超80亿美金,可以说是全球生物医药创投圈的一线玩家。
而海外基金方想找BFC Group做的“新模式”,以及恒瑞和康诺亚的出海选择,就是“NewCo”,即将公司核心产品的海外权利(ex-china right)授权给海外成立的新公司,同时引入海外基金,搭建国际化管理团队,以公司海外上市或被并购实现退出。
现在资本情况比较冷淡,比较低谷。不论是A股和港股,还是纳斯达克,近三年biotech IPO的数量和金额都在持续下降。今年上半年,A股和港股的IPO数量和募资金额都非常少,纳斯达克有10起,医疗行业有回暖趋势,但跟过去十年没法相提并论。
这种时候对于biotech和投资人来说都是个非常艰难的时刻,大家不知道有什么样的出路。其实现在除了并购,还有另外一个选择,能够通过海外市场退出——NewCo。
不论处于什么阶段的创新药资产或公司,BD都是一个永动机,能够帮助公司持续运营、补充现金流,通过BD,将核心资产的海外权利(ex-China right)授权给海外设立的NewCo,在海外基金和国际化管理团队的运营下上市或被大药企收购,让投资人实现退出。
一般来说,从药企与海外基金共同成立NewCo开始,海外基金会花4个月左右的时间尽调、组建国际化的管理团队、引入更多投资者,接下来6~12个月进行技术转移(tech transfer),之后开始海外临床试验的入组准备工作,最快一年就可以在纳斯达克上市。
假设国内创新药企在NewCo成立时占有40%的股权,NewCo上市后仍持有20%的股权,并享有10%的royalty,那么在NewCo利润率为40%的情况下,这家国内创新药企共计占有这家NewCo——或者说这款license-out产品的海外市场——40%~50%的价值。
在这个过程中,海外基金会提供资金,帮NewCo招募顶尖的管理团队来运营,推动海外上市。这都是海外基金非常熟练的事。
另一方面,这些基金在参与孵化NewCo的时候,其实心里都非常清楚将来的买家是谁,甚至可能已经和买家有过初步的沟通圣诺医药2000万美元打水漂;荣昌生物现金流已经耗尽;美元投中国创新药玩法变了共三条快讯,商量大概研发推进到什么阶段就可能被收购,而且在这种情况下,100%溢价收购也是很常见的。
就在上个月,恒瑞医药和几个大的海外基金做了这么一家NewCo。license-out和NewCo的成立是同时发生的。
除了总计约60亿美元的首付款、里程碑付款和销售里程碑款,恒瑞医药得到了Hercules 19.9%的股权,其他海外基金占有70%的股权,还有10%ESOP给管理团队。
首先是今年上市的ArriVent及其背后的艾力斯。三年前的2021年6月30日,ArriVent同时宣布公司成立、获得1.5亿美元A轮融资、从艾力斯授权引进第三代EGFR-TKI,拥有其中国外的海外权利。
在这笔交易中,艾力斯获得了4000万美元首付款、累计不超过7.65亿美元的研发和销售里程碑款项、销售提成费(royalty)以及ArriVent一定比例的股份。
管理团队上,ArriVent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Zhengbin(Bing)Yao博士)有过运营biotech并成功被MNC并购的经验。他曾在2018年联合创立Viela Bio,担任董事长及首席执行官,Viela Bio于2019年纳斯达克上市,2021年被Horizon Therapeutics以约30.5亿美元的价格收购。有这么一个成功的case之后,再去运营一家新的公司,成功率就非常高了。
2021年成立后,ArriVent只有伏美替尼这一个核心资产,估值是4500万美元。2023年,ArriVent在美国进入临床II期试验,3月完成1.55亿美元B轮融资,包括很多国际知名基金,10月获FDA授予伏美替尼“突破性疗法认定”。
2024年1月底,ArriVent正式在纳斯达克上市,募资1.75亿美元,估值6亿美元。此时它在美国的临床试验已经推进至III期,预计在2025年8月完成。在IPO后,艾力斯仍持有4.2%的股份。
同时不少海外基金参与孵化,搭建了一个在疫苗领域非常有经验的管理团队:CEO是Seagen之前的BD负责人兼CSO;CMO是来自于Takeda疫苗业务的临床开发负责人;COO和监管方面的负责人都来自于GSK疫苗部门;CTO是前catalyst生产方面的负责人。
由这么一个团队组建的一家公司,可想能够以最快的速度将诺如疫苗产品推进到临床,推动公司上市。
实际上,Hillevax成立不到10个月的时间就在纳斯达克上市,而且是2022年纳斯达克biotech里发行规模最大的。上市的同时,Hillevax启动临床,2023年已经完成3000多个婴幼儿的入组。
除了license交易和股权可以让公司收获更多的经济回报,NewCo会围绕license-in的核心资产建立最顶尖的管理团队,而且完全聚焦于这个核心资产,这个产品成功,这家公司就成功,管理团队就成功,背后投资人就成功。
与license-out给大药企或biopharma相比,后者可能随时会战略调整,但是以NewCo的方式,这个资产始终处于绝对优先级。
第一,有一个顶尖的管理团队运营NewCo,不管是临床还是监管,海外路径都非常清晰,确定性比较高,而且由于就做一个核心产品,执行起来也很快,会不断有进展,也会给中国投资者正面的反馈。
第二,现在国内上市公司对于资产的海外价值给得相对比较低,通过NewCo的方式也可以促进我们二级市场的投资人真正意识到公司所持有的海外价值。
大家可能会想,既然NewCo这么好,为什么不能我们自己做,包括建立团队、融资,为什么要把股权给其他人,让其他基金来孵化?
这就涉及到是不是有能力去招募全球顶尖的管理团队,是不是自己有这个能力能够快速找到这些顶级基金进行IPO,确定性有多高。
为什么海外基金“操盘”的确定性那么高?因为这些基金在组建NewCo的时候就基本确定了IPO的募资金额、知道IPO的时候可能有哪些投资者,上市之后,一旦临床数据出来,股价很可能会成倍飙升;其次海外的MA市场也非常成熟,通过这些有经验的管理团队运营,MA的可能性、成功率也会更好。
荣昌生物20CM跌停,原因简单,靠银行借钱续命,股价见中报必死。计息银行借款(短期借款+长期借款)2023Q4比2023Q3增加4.8亿元,2024Q1又比2023Q4增加4.5亿元。
荣昌生物2024Q1货币资金仅剩6.2亿元,如果没有银行援手,现金流已经耗尽。
复盘荣昌生物(详见《医药三只灰犀牛》、《明星药企失速》),我们发现一个诡异之处:这家公司研发、经营迄今表现正常,该做的都做了。
研发、商业化进展正常,2008年公司创立,2021年两大明星产品上市,维迪西妥单抗(RC48)为首个国产ADC药物,泰它西普(RC18)为全球首款BLyS/APRIL双靶点生物制剂;融资能力高于正常水准,2020年、2022年先后在港沪两地上市,募资净额63亿元;BD能力高于正常水准,2021年维迪西妥单抗以2亿美元首付款26亿美元交易总额授权给Seagen,创单药海外授权新纪录;关键性临床试验正常,核心管线没有翻过车;甚至高管薪酬都在正常范围内,2023年,首席执行官房健民、首席医学官何如意的薪酬(不含股份支付开支)分别为814万元、772万元。
荣昌生物按照一家Biotech的正常流程发展,所有风口都赶上了,但为何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
当他们都开始跑,你还在走;当他们都开始卷,你还不卷。荣昌生物低估了生存环境的压力,更无视生存环境的恶化。在一片泥沼地里,没有优雅的转身可言,常规表现是远不够的,你不能出一次错,只有做到极致才能活下去。
1998年,常兆华回国创立微创医疗。10年后,房健民回国创办荣昌生物。两家公司都有着不合时宜的松弛感。
如果美好瞬间可以变成永恒,海归科学家们愿意把2021年上半年生物科技的盛况,永远延续下去,可惜不能够。
当Biotech普遍收缩保命时,荣昌生物仍在扩张,2023年在职员工3615人,比2022年增加283人,2023年亏损15.11亿元,比上年扩大51%。
比你优秀的人,比你还努力,未必是一句毒鸡汤。2023年研发开支,荣昌生物同比增长33%,而信达生物同比下降22%,康方生物同比下降5%。2023H1商业化团队人效,荣昌生物约35万元,百济神州约190万元。
荣昌生物对烧钱有自己的合理解释,多个创新药物处于关键试验研究阶段,加上海外遍地开花,导致研发费用大幅增加。随着泰它西普和维迪西妥单抗的准入医院数量及覆盖药房数量大幅度增加,商业化团队一线销售人员扩充以及商业化推广力度加大导致销售费用相应增长。
截至2023年末,荣昌生物港股募集资金已使用98.86%,仅剩4322万元。A股募集资金已使用95%,仅剩1.96亿元。共有八个分子处于临床开发阶段,预计总投资规模59亿元,累计投入金额31亿元,仍需投入28亿元。
直到7月9日,荣昌生物仍执信泰它西普、维迪西妥单抗的造血能力,在投资者电话会上表示“商业化带来一定规模的现金流。”
事实上,2023年荣昌生物产品收入10.49亿元,同比增长42%,而销售费用同比增长76%,这意味着以高销售费用强推产品。2024Q1荣昌生物营收3.3亿元,环比增长5%,泰它西普、维迪西妥单抗各自距离10亿门槛还很遥远,已经未老先衰,爬坡吃力。
荣昌生物养着自免商业化销售团队约750人、肿瘤商业化销售团队约600人,产品收入尚无法覆盖营业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谈何造血能力?
两大明星产品未成爆款,有支付能力的因素,也有临床获益的因素。荣昌生物的问题在于仍常规操作、惯性漂移,未及时对临床开发策略进行优化和切割,以致于骑虎难下,窟窿越来越大。
泰它西普号称同类首创BLyS/APRIL双靶点新型融合蛋白产品,其实也是跟随式产品。首个靶向BLyS/APRIL双靶点的生物制剂是Atacicept(阿塞西普),与贝利尤单抗几乎同步进入临床研究,最初由ZymoGenetics研发,后转让给德国默克,命途多舛,先是在2009年折戟多发性硬化症,2016年SLE(系统性红斑狼疮)IIb期临床又遭遇失败,随后被默克雪藏,2020年11月转让给Vera Therapeutics。泰它西普在Atacicept的基础上优化设计,药理学特性的提升,为临床试验成功打下基础。
目前获批SLE适应症的生物制剂,仅有葛兰素史克贝利尤单抗、荣昌生物泰它西普和阿斯利康Anifrolumab(阿尼鲁单抗,仅在美国上市),但都没能成为爆款。贝利尤单抗2011年获批上市,2022年全球销售额为11.46亿英镑。阿尼鲁单抗2023年销售额2.8亿美元。
据弗若斯特沙利文,2020年全球SLE患者数量约780万人,其中,中国约103万人。患者基数庞大,治疗需求迫切,药物竞争格局良好,为何卖不动?中重度SLE患者脏器已经受损,3款生物制剂对其治疗效果都比较疲软,暂时缓解症状,延缓病程,并且效果因人而异。
SLE一次性治愈还需期待CAR-T破局,两项学术研究表明,治疗后80%的患者SLEDAI-2K评分降至0分,自身抗体实现血清学转阴,并达到持久缓解,最长达44个月(近4年)。
CAR-T用于治疗SLE商业化还需要3到5年,费用有望降到30万-50万。
泰它西普SLE适应症海外III期临床第一阶段于2023年底完成患者入组,第二阶段已启动。泰它西普MG、pSS、IgAN适应症均进入海外III期临床。
海外III期临床是双刃剑,如果缺乏直接商业化能力,又不能及时BD出去,将是沉重的费用负担。截至2023年底,泰它西普研发累计投入13亿元,还将投入近10亿元。
维迪西妥单抗卖不动,也是因为临床获益不显著,而且在第一三共ADC神药DS-8201挤压下,拓展前线治疗和新适应症的空间已不大。维迪西妥单抗在新药申报策略上取巧,成为首个国产ADC后,其实已经兑现大部分价值,但野心膨胀,还有13项临床研究正在推进。
把过多资源浪费在竞争力较弱的产品(主要是维迪西妥单抗)和陈旧的ADC技术平台上,荣昌生物困在昔日的光环中不能动弹。
创新药在中国是全新事物,大家都没有经验,而且都不可避免存在路径依赖、认知局限,分不清beta红利、alpha能力,所以,不能苛求荣昌生物先知先觉、全知全能。
但市场并没有一丝同情心、同理心,创新药的生存环境是如此严酷,以致于Biotech每一步都不能出错,常规表现还远不够,不做到极致是活不下去的。
太难了,如果荣昌生物最终定增募资25.5亿元,加上两次IPO,90亿元还不能砸出一个成功的创新药企的话,那真是价值毁灭的惨案。
其实,这还不是真正的绝望,另有一家Biotech,什么都没做错,在力所能及的每个方面都高于正常水准,但正在走向宿命的终点。希望其能够大逆转,不给人们总结分析的机会。